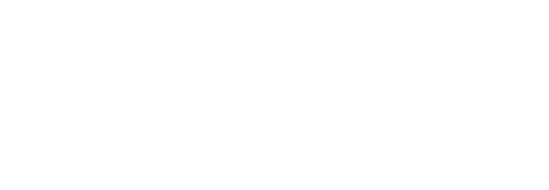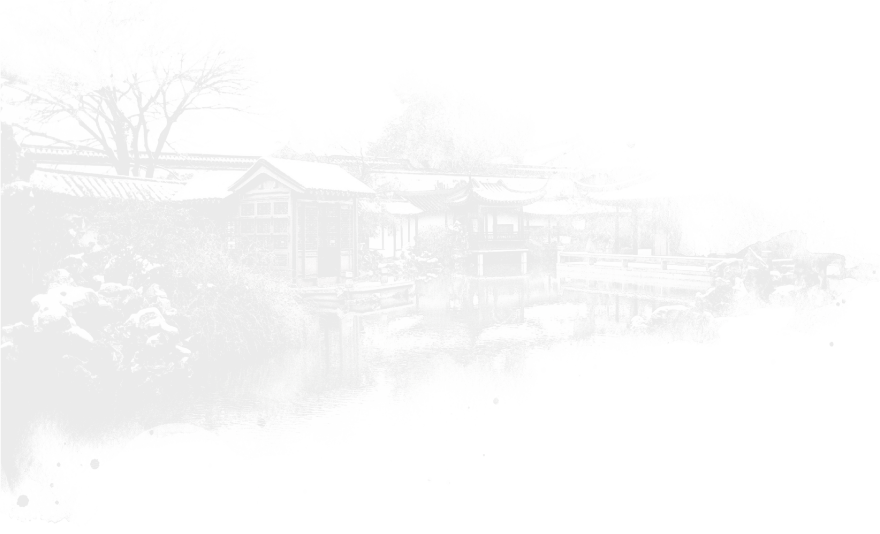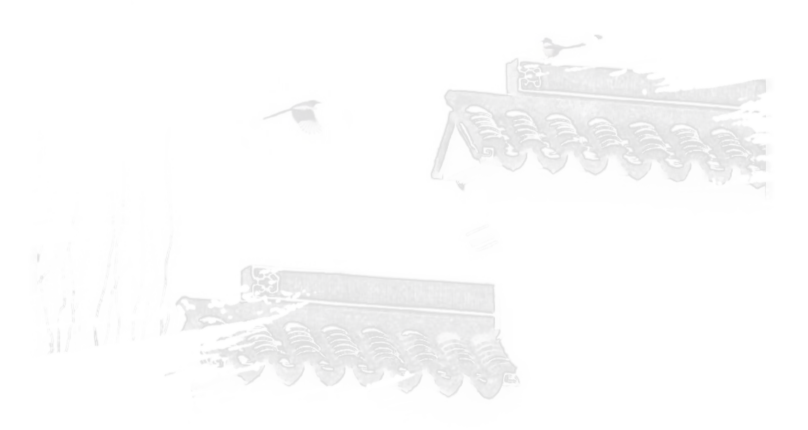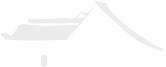景区游客承载量公告: 瞬时承载量6万人次
日承载量9万人次
实时客流715人次
舒适度:舒适
景区游客承载量公告: 瞬时承载量6万人次
日承载量9万人次
实时客流715人次
舒适度:舒适



 400-698-2990
400-698-2990
 景区游客承载量公告:
景区游客承载量公告:
715
实时客流
6万
瞬时承载量
9万
日承载量
舒适
舒适度
停车场:剩余:1000/总:1000
400-698-2990

景区动态
THE DYNAMIC OF THE SCENIC SPOT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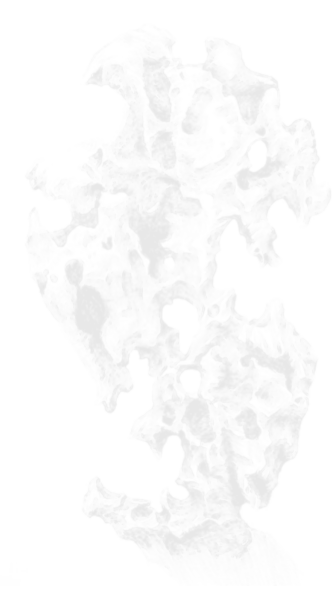

世界同里
ONE WORLD AT A TIME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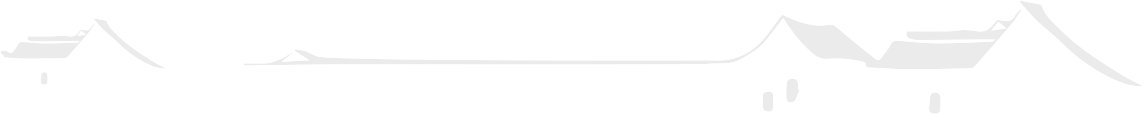

同里古镇地处太湖之滨,大运河畔,距苏州18公里,距上海虹桥机场80公里。东南接318国道、苏同黎公路,西连苏嘉杭高速公路和227省道,地理位置优越,水陆交通便捷。其中古镇区面积为0.87平方公里,居民11161人,同里是水上天堂,大小湖荡星罗棋布,河港交错,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40.3%。
据考古证实,同里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“崧泽文化”和“良渚文化”时期。早在新石器时代既有先民在此刀耕火种、生息繁衍。优越的自然条件,使这里成为吴地最富庶的地方,因此同里旧称“富土”。唐初改名为铜里,宋代正式建镇后,将旧名“富土”两字相叠,上去点,拆分为“同里”。
优越的自然环境,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同里灿烂的人文。据史料记载,自北宋到清末,先后出过共出状元1名、进士45名、举人95名。如南宋诗人叶茵,明代《永乐大典》副总纂修梁时,《园冶》作者、杰出的造园大师计成,清代吴门画坛一代宗师陆恢,军机大臣沈桂芬,近代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去病,著名国学大师金松岑,社会活动家王绍鏊、蓝公武,《文汇报》创始人严宝礼,著名经济学家金国宝,革命烈士著名教授费巩;当代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冯新德、沈善炯等。
同里镇1981年由国家建设部批准列为国家级太湖风景区13个景区之一,1982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,1995年被列为首批“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”,2000年古镇内的清代园林退思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,2003年被国家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评为“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”,2010年同里景区被评为“国家AAAAA级”旅游景区。